最近,有一位网友在我的评论区发表了一番言论,他显然对彼得罗颇有同情,同时又以一种闪烁其词的方式讨论叙事学,这反而让我领悟到不少男性读者是如何解读《那不勒斯四部曲》的。他们倾向于在书中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的精神支柱,比如彼得罗和他的父亲圭多,并将其视为虚构世界中的绝对智者。这位读者将彼得罗对莱农的看法当作金科玉律,但实际上,作者并没有通过任何角色来评判莱农,而是让每个角色根据自己的经历说话,并做出与他们生活轨迹相契合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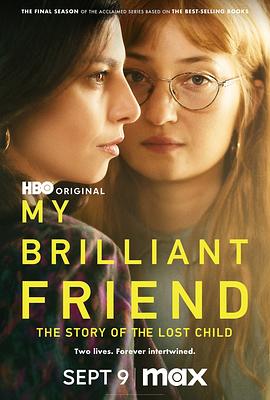
彼得罗曾经形容莱农是一个“半……主义者”,这是因为莱农体内融合了两种语言、两种文化,既有标准意大利语也有地方方言,既有那不勒斯老城区的野蛮气息也有知识分子的优雅风范。她之所以只能是“半……主义者”,是因为她的另一部分并不适应“主义”这样的学术术语。我喜欢书中描写莱农在大学期间使用从老城区继承的手段反击同学、保护自己的一幕,这正是她内在的另一面力量的展现,即便是后天的教育也无法掩盖这部分。彼得罗之所以这样看待莱农,是因为他自己只有一种语言,一直生活在固定的社会阶层中,因而只能理解和接受属于他那个世界的“半个莱农”。他虽然意识到莱农的另一面,但却无法理解其复杂性和根源所在。
彼得罗最初追求莱农的原因在于,她的卑微出身让他感到安全,使他能以教授的身份居高临下地观察平民生活。然而,当莱农开始表达自己的欲望时,两人的关系便无法继续下去。艾罗塔家族帮助莱农出版小说并非出于无私,而是为了让儿媳的地位与家族相称。如果说莱农对家族的帮助、对彼得罗的感情有所亏欠,这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事实上,这一切都建立在相互受益的基础之上。
如果要在彼得罗和尼诺之间进行比较,那么前者可能比后者更具危害性,因为尼诺这类向上攀爬的人内心充满脆弱与不确定,一旦女性洞察到这一点,便能看穿他虚假的魅力。而彼得罗则凭借其优越的出身,自始至终保持着知识权威的形象,这让他能在革命浪潮中坚守原则,不受一时流行观念的影响。然而,这种固有的自信背后是狭隘的视野和顽固的态度,而且即便莱农与彼得罗离婚后,艾罗塔家族的影响力依旧无处不在。
尼诺至少还需要伪装成尊重女性的样子,而彼得罗则毫不掩饰地拒绝采取避孕措施,要求莱农放弃个人事业投身于生育和家务。圭多也能堂而皇之地将阿黛尔贬低为一个挂在他姓氏下的妻子,并对莱农辛苦抚养的孩子说:“你们是艾罗塔,而你们的母亲只是格雷科”。
(如果有人读到这里认为我在为尼诺辩护或赞扬他,那我只能说这样的阅读理解能力实在令人无语。)
如果莱农能够在满足自身欲望的同时承担起对女儿的责任,那自然是最好的结果,但在作者描绘的那个年代背景下,显然缺乏孕育这种理想人格的土壤。女性受到新旧思想的冲击,处于探索自我的过程中,因此,莱农未能成为一个完美的榜样。
既然男性读者喜欢将自己代入艾罗塔的角色,那么不妨让我们也从莱农或阿黛尔女儿的角度来看看。这两位女性在面对情感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们都有婚外情的行为,但莱农选择了离开原有的婚姻关系,而阿黛尔则选择维持婚姻和家庭。如果我是她们的女儿,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责怪莱农沉迷于自己的情感需求,忽略了对我情感上的照顾,使我生活在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或许会更认同莱农式母亲的价值观,这让我明白自己也有权利追求个人的幸福,不必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而阿黛尔呢?她和她的女儿玛丽娅罗莎一样,充满母性,牺牲自我去维护家庭或某个人,但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预示。既然在那样的年代里找不到符合现代理想的母亲形象,我宁愿选择一个让我知道我也能够反抗、能够忠于自我的母亲。
总有一些男性追随权威的声音,他们一生都在努力成为权威的附庸,并以此来压制不同意见,就如同那位评论区的网友试图用他并不精通的叙事学理论来打压我的独立创作(所谓的独立创作正是拒绝模式化的表达,体现个人特色)。他们不会对托尔斯泰说“你小说中的哲学思想不够系统”,也不会对沈从文说“你的散文对湘西民俗风情的描绘不够严谨”,他们只会要求一个擅长中式烹饪的厨师去做西餐。质疑女性写作的规范性是打压女性创作的传统手段。可惜的是,这种伎俩在我这里行不通,不论他们多么坚持。
某些男性读者之所以偏爱彼得罗而非尼诺,并不是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看到了尼诺对女性的利用(他们这么说不过是贼喊捉贼),而是因为尼诺的外表符合女性的审美标准,而女性审美意识的觉醒降低了他们的社会评价。尼诺表面上鼓励女性追求自由,即使只是表面现象,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过分的妥协。而彼得罗则是天生的特权阶层,拥有他们梦寐以求的一切。他们自身如同尼诺一般自卑脆弱,却崇拜艾罗塔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威,没有坚定的核心信念,害怕在尼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
赞美彼得罗依靠家族获得的从容不迫,推崇他无需亲身经历艰辛、埋头于书斋的学者身份,鄙视莱农跨阶层的努力与困惑,全盘否定帕斯卡莱未经知识洗礼的理想主义——这些都是导致我们的社会进一步衰退的观念。
 七弟电影
七弟电影
![韩国丧尸片《#活着/ALIVE》百度云网盘资源[HD-MP41.7GB][完整版][高清韩语中字]-七弟电影](https://gaga.pochou.com/wp-content/uploads/2020/06/活着-电影剧照-5-300x300.jpg)

